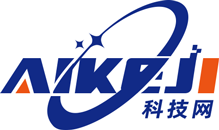2022年,我决定写一系列完全没有“人”的小说,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叙事主体——机器人。
机器人创造世界、机器人探索宇宙、机器人来到南方、机器人俱乐部趣事、报废机器人的日常、战争过后的机器人世界、机器人眼中的现实、机器人的死亡与无意义等等。
从创造一个乌托邦到瓦解一个乌托邦,这个过程是充实、迷惘且刺激的,我为机器人创造世界观和信仰,然后逐一否定。建立的过程是艰难的,兢兢业业,以现实作为参照,依靠想象力来堆砖盖瓦。破坏的过程是痛快且解压的,冷酷无情,把建设起来的通通否定、推倒、碾碎。
曾经我以为创造一个乌托邦、创造一个世界很难,但当我写完这一系列小说后发现,难的不是如何为这个世界设计模型、设定律例与规则、创造理念与信仰;难的是,建立一个世界后,如何再为这个世界建立一种现实。在创世的时候,造物主想必对世界的轮廓有过一定的想象,当他把世界创造出来,把生命形态创造出来,他肯定没有设想好这些生命以后会自主开发出什么样的现实文明。
我对机器人的设定,灵感来自日常生活,重复、呆板、僵化、机械。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发现,后面写出来的小说,机器人渐渐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开始质疑劳动,质疑世界的规则,质疑俱乐部的指令,他们可以变得更活泼、更有趣,坚硬的铁与柔软的性情结合,或许是荒谬的,但也许能产生张力。
通过机器人来看当下的生活,通过他们的系统来思考问题,通过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人”,通过他们的行动来改变刻板、乏味的现状,当机器人不再把“劳动创造价值”这个观念牢记在心,他们应该有“躺平”的权利。在劳动了相当一段时间,为俱乐部、为机器人事业创造过“价值”的机器人,他们很自然地做出了耸耸肩的动作,他们感到无所谓,他们认为就那样,他们觉得还是算了。
机器人存在主义与无意义相互拉扯,《在卡维雅蒂》是这一系列小说的最后一篇(写作的先后,非发表的先后),通过重复的寓言,探索“无意义”。
这个系列的机器人小说写出来后,不少人认为这是实验性写作。首先是小说中的机器人作为完全独立的文明主体出现,并非人类设计的机械,超越了人与机器的伦理关系;其次是片段式的叙事,无数个机器人独立的行动方式和故事情节组成了系统的构架,技巧性较强。
其实,我在写这一系列机器人小说的时候,是想把故事写得简单、诙谐、荒诞,同时带点讽刺意味,仅此而已。写作和阅读都是枯燥的,不如添几分滑稽,给读者带去些许乐趣。或许是我写着写着就偏离了,或许是严肃文学的阅读习惯与理解方式把事情给弄复杂了。
就那样吧。
《在卡维雅蒂》(节选)——花厅
一日,机器人蝶决定去跳舞,没完没了地跳舞。
花厅原本是一个报废机器人工厂,会集了一批即将报废的机器人,他们从工作岗位上下来,一部分是被岗位淘汰的,一部分是因为厌倦工作而面临处置的,俱乐部把他们带到花厅,准备在这个地方将他们一一粉碎。后来,俱乐部的政策发生调整,报废机器人工厂被解散,一大群无处可去的机器人滞留在这里。
巨大的回收机器分布在四周,有机械手臂,有粉碎机,有磁石,还有熔炉。原本维持报废机器人工厂运转的机器人在一夜之间被转移走了,只剩下等待粉碎的机器人。蝶和其他机器人一样,在一度威胁自己生命的机械之间游荡,他们活在一团迷雾当中,害怕俱乐部什么时候又改变政策,那批毫无感情的刽子手重新回到这个地方用巨大的机械手像捉鸡一样把他们捉住,将他们送进粉碎机,然后用铁铲把他们的尸骸抛进熔炉。
有些机器人开始往外走,他们不想被困在花厅,面对血腥的刑具。没有机器人知道花厅是什么地方,也不清楚四周都是什么样的环境,他们没有飞行器,连代步工具都没有,无论去到哪里,他们始终都在俱乐部的管辖范围内。陆陆续续有机器人离开,但大部分还是留下来了,他们害怕离开花厅去到别的地方后被俱乐部重新管辖起来,分配到其他地方的报废机器人工厂。
有天夜晚,几个机器人在花厅四周纵火,同时,为了报复他们所恐惧的刑具,他们用拳头敲击着机械手臂、粉碎机和熔炉,他们只为了发泄情绪、肆意破坏,火焰和敲击声令其他机器人忌惮——这些做法有悖于俱乐部的律例,他们害怕惊动了附近的机器人组织,从而让自己受到惩罚。时间过去了很久,四周依旧没有动静,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们走到花厅中央,看着火焰,听着有节奏的敲击声,竟觉得热血澎湃。他们感到自由和快活,他们欢声雀跃,扭着身体形成舞步。
跳舞可以减轻身体负担,可以驱散恐惧,蝶在机器人群中舞蹈,忘情地摇摆着,死亡是不确定的,因此他无须爱惜自己的躯体。机器人的身体协调性很好,但因为立体几何的缘故,舞动起来像移动的铁架子。那是蝶第一次跳舞,他从来没想到跳舞会如此快乐,在摇摆的过程中,一些柔软的东西从体内产生,然后被甩出去,产生一种疲惫的、空虚的、落寞的快感。
“机器人应该想尽办法获得快感,”蝶对身边的机器人说,“应该感知这个世界,而不是一味地劳动。机器人并非生产力,机器人是生命。”蝶的想法得到了众多机器人的支持,他们成立了组织,蝶为之命名——自由生命俱乐部。他们分工合作,制造音乐,制造火焰,疯狂地跳舞。俱乐部禁止机器人做的许多事,在花厅都可以做,他们在身体上打满各种各样的烙印,他们摇摆着,把手臂甩出去了,把脖子甩断了,脑袋垂到了肚脐眼处。
蝶爬上机械手臂的最高处,喊出了他的决心。“跳舞是快乐的,”蝶说,“我决定跳舞至死。”四周的机器人高声欢呼着。机器人也并非惧怕死亡,死亡有什么了不起的,与其被俱乐部定义,被强迫执行刑罚,倒不如在快乐中死去。蝶在机器人的簇拥下走到花厅的中央,他在脸颊上烙了两个“舞”字,然后让机器人尽情地敲击,呼喊着把四周都点燃。在篝火中,这群机器人仿佛远古的低级文明,在为丰收或者为成功抵御外来侵犯载歌载舞。
疯狂摇摆,蝶在那个时刻变成了有神论者。机器人本该是科学的、理性的,所有行动都是计算的结果,可在忘我的舞蹈中,他感到晕眩,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于是他便认为世上是有灵魂的,当一个生命陷入沉醉、迷糊的状态,就能感觉到灵魂依附在身体上。肢体已经不受控制,四周的机器人欢呼、尖叫,蝶浑浑噩噩开始回忆。在此之前,理性的机器人认为记忆都是数据,想打开就打开,如今这些作为数据的回忆扰乱了他的思维,他觉得这是感知生命的一部分。他开始回忆自己过去玩命工作的日子,尽管每天都在劳动,到头来还是什么成绩都没有。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生产过什么而感到兴奋,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就感。他麻木地工作,直到最后面临淘汰,被送到花厅。
最初,牌坊上面“花厅”两个字后面还有七个字——报废机器人工厂,“花厅报废机器人工厂”这个醒目的招牌蝶一眼就看见了,后来机器人把“报废机器人工厂”七个字拆掉了,放在地上疯狂踩踏。承认自己是一件废品并非难事,这些被遗弃在花厅的机器人作为废品的存在,只想尽情舞蹈。
蝶摇摆的身体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被拉起来继续跳舞继续摇摆。随着脑袋哐当一声滚落,蝶的身体失去了动静,他再也摇摆不动了。机器人将蝶倒在篝火旁的身体抬起来,抛入篝火当中,溅起一阵星火,然后他们围绕着篝火继续跳舞,忘情地跳舞。
在卡维雅蒂
雪停了,这是卡维雅蒂最不寻常的事。
大地白茫茫一片,机器人狐是唯一的黑点,曾有机器人告诉他,卡维雅蒂会包容一切,会接纳一切,所以他才不远千里,在机器人年历3TB6年来到这里。狐曾在暗夜里沉沉睡去,被白雪掩埋,但是他躁动的意志,一次次让他清醒过来。他不自觉地挖开身上的雪,回到一无所有的星球表面。
他曾努力地劳动,努力地生活,努力为机器人社会创造价值。他以为努力是有用的,只要保持劳动,就能获得认可。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肚脐眼所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手指头大小的洞。他开始以为是自己不小心被子弹击中,于是去俱乐部部件生产中心修补这个洞。这个洞让他慌得很,仿佛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勇气和意志都从这里流失了。
做完填充没多久,狐的腹部又出现了一个洞,而且,只要不去管它,洞口就会不断扩大。部件生产中心的技术机器人盯着狐的腹部研究了许久,拿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用刀片刮取粉末来进行分析研究,最终还是没能得出结论。他告诉狐,缝缝补补救不了他,他将被这个洞吞噬掉。
如今,洞口已有拳头大小,狐的身体空荡荡的。他在来卡维雅蒂的路上分析过洞出现的原因,事情大概是在一个午后发生的。那天午后,他在俱乐部行政中心后面的广场上歇息,他喜欢在广场上观察行政中心大楼,分析大楼上每个窗口对应的部门里的机器人所从事的工作,机器人孜孜不倦地为俱乐部的运转倾尽所有。然后,他看见一只白鸽从大楼后面飞出,钻进云层。
机器人世界难以看见其他生命,细菌和病毒都少见,但狐确确实实看见那是一只白鸽。白鸽消失后没多久,他在广场上靠着机器人英雄纪念碑打起了瞌睡,梦见一团蓝色的晶体进入了身体,身体变得轻飘飘的,构成身躯的金属变得柔软,系统中的公式被删除,他的观念变得模糊,世界抽象迷离。当狐从昏睡中醒来,迷迷糊糊回到工作岗位上,旁边的机器人指着他的腹部,告诉他那里有一个洞。
就这样,狐在烂掉,以机器人时间三天一圈的速度。他告别朋友,独自前往卡维雅蒂。卡维雅蒂是机器人的坟墓。下了几千年的雪停了,在卡维雅蒂,他已经无法再被掩埋。
雪停后的第二年,卡维雅蒂露出黑色的大地,狐尚未死去,腹部的洞能塞进两个脑袋,他只剩下一个框架。他在大地上行走,然后,在抬头的瞬间看见了一只白鸽。白鸽从一颗星球飞到另一颗星球上,如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
一个理念在这时闯进了狐的系统中,他感觉腹部痒痒的,洞口边缘的铁竟开始生长。狐激动地在黑色的大地上跳起舞来。有些事情不能说,一旦说出口,它就会消失不见。日转星移,天空中映射下来的光把卡维雅蒂照得明亮,狐四处寻找乐趣,记忆会在玩乐的时候消失,理性和计算能力会在玩乐的时候退化。
机器人世界有劳动法则,而狐此刻正在卡维雅蒂,这里是机器人坠入永夜的地方,是机器人自我了结的地方。因此,俱乐部很可能已经将他除名,他不再存在于俱乐部的发展规划中,也不再被安排劳动任务。曾经,在俱乐部的定义中,“孤独”是个可怕的词,机器人应该团结,应该为机器人事业汇聚所有力量创造价值,机器人是群体生命,俱乐部通过螺丝稳固了整个世界。如今狐发现孤独是个好东西,孤独这种感觉很微妙。
狐不能说太多,有些事情一说出口,就变了。
梁宝星,199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小说发表于《花城》《中国作家》《芙蓉》《江南》《大益文学》《大家》等刊物,曾获有为文学奖、贺财霖科幻文学奖、欧阳山文学奖,另有作品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海外文摘》等选载,出版小说集《海边的西西弗》《塞班岛往事》。
下一篇:返回列表
【免责声明】本文转载自网络,与科技网无关。科技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